搜索


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張雙虎
35年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以下簡稱青年基金)項目設立之初,曾為一個年輕人“保留”了1年🚎。
緊接著🦁,他氣勢如虹,獲得優秀中青年人才專項基金項目和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
此後,因為想法“新奇”,無法取得評審專家認可🦷,在數次申請“失利”後,得到一個非共識項目專項基金(當時稱科學部主任基金)資助。
在此基礎上,他厚積薄發➝,將一個“非共識”科學問題拓展為國際前沿熱點領域……
談起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結緣的那些往事🧪,中國科EON4院士、EON体育4教授鄧子新感慨萬千:“我的科研生涯差不多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發展同步,也經歷了自然科學基金人才資助體系的各個階段,應該說和科學基金共同成長……”

鄧子新


鄧子新(前)指導學生做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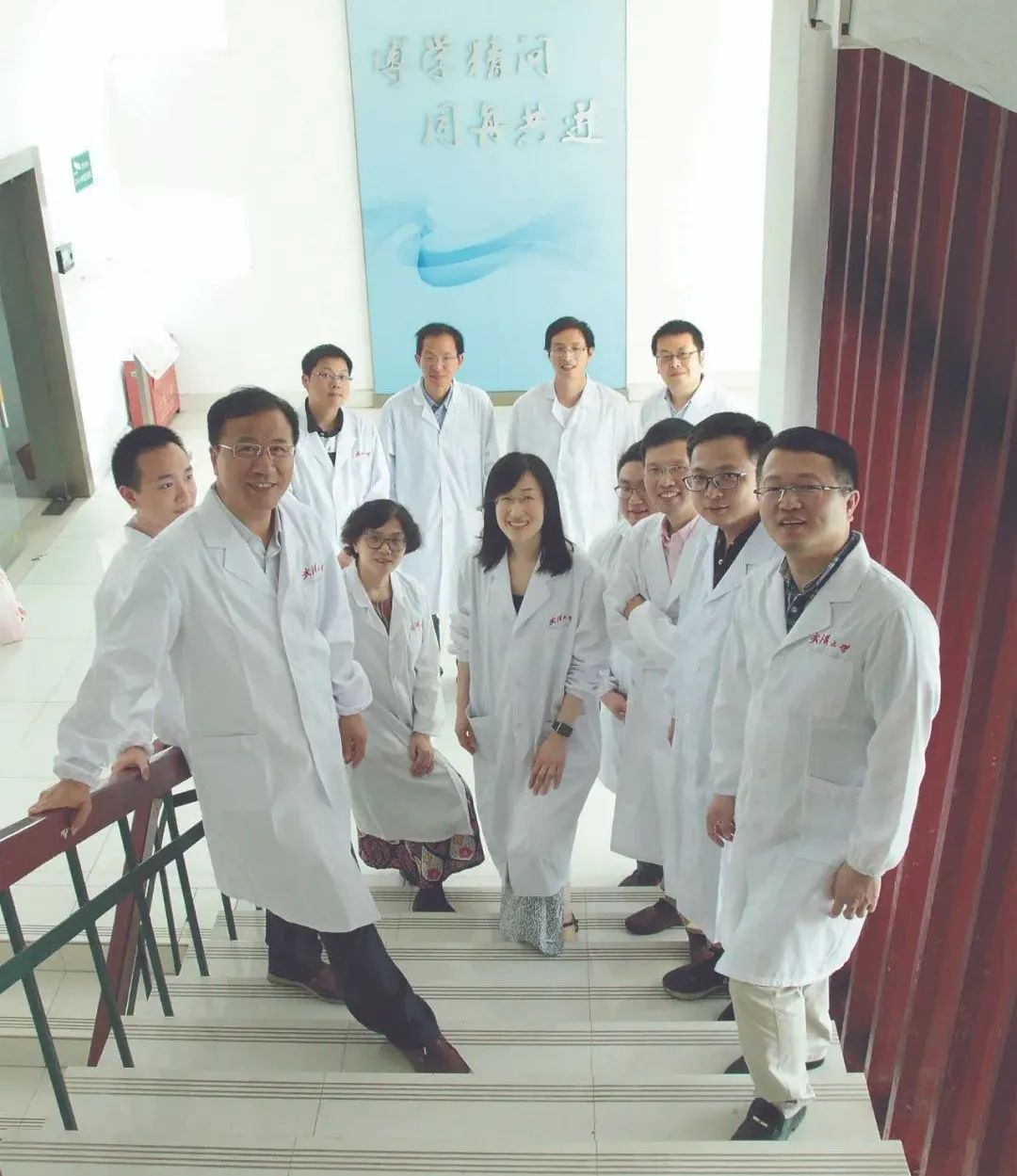
鄧子新(左前)和學生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開啟科研生涯
1987年,鄧子新還在英國約翰·因納斯研究中心深造。
這裏是世界鏈黴菌遺傳學發源地,他的導師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分子生物學權威戴維·霍普伍德爵士。
有一天,研究中心來了一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工作人員🪸🧝🏻♂️。
這位工作人員在駐英大使館教育參贊陪同下,作了一段簡短的交流,介紹了一些國內最新的科研環境和資助政策。
鄧子新由此了解到,從1987年開始,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了青年基金,專門資助從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和部分應用研究、年齡在35歲以下👩🏿🎓、已取得博士學位(或具有同等水平)、能獨立開展研究工作的青年科學工作者。
即將完成博士學業的鄧子新非常興奮——如果能申請到這項科學基金,回國後馬上就可以開展工作了🧗🏻♂️。
因此🐞,他立即和國內合作的老師商量🫄🏿,提出一個研究方案並遞交了項目申請書。
“當年的評審蠻迅速的。”鄧子新回憶說,“首期青年基金的資助額度是5萬元🧚🏿♀️,得到申請批準的消息後我簡直‘欣喜若狂’,激動的心情不亞於今天獲得幾百萬元的資助。那時候國家總的科研經費很少,能夠拿出專門經費資助年輕人很不容易,所以我當時更加堅定了回國的決心👰🏿。”
獲得博士學位後,導師戴維·霍普伍德對鄧子新寄予厚望📽,不但希望他的科研事業能很好地發展,也希望分子生物學能夠在中國得到充分重視。
他為了支持鄧子新通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申請到的一個幾萬英鎊的資助項目🐉,決定派7位著名學者😅,按照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EMBO)的水準,到中國舉辦一個基因工程實驗操作技術培訓班。
當時中國的科研基礎相對薄弱,實驗室用的冰箱、離心機,甚至微波爐都要從國外購置。
設備購買和培訓班籌備工作在今天看來都不算什麽,但在當時卻要經過一系列繁瑣的審批手續👼🏿。
鄧子新只好在英國又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
1988年🌯,在全國“出國潮”湧動的背景下,鄧子新“逆勢”歸國,回到母校華中農業大學,用一年前申請下來的5萬元科研啟動經費😨,開啟了研究生涯🂠。
“那時候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5萬元能辦不少事。”鄧子新說🧔🏼♂️,“今天我和團隊在學術上取得的成果,跟當時那5萬塊錢密切相關。”
從非共識項目到熱門領域
1993年,青年基金結題前⤴️,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優秀中青年人才專項基金,鄧子新成為首批獲資助者;1994年,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設立,他仍然是第一批獲得資助的學者♊️。
在科學基金申請方面👩🏼🦳,鄧子新一路走來👰,可謂無縫銜接、順風順水。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等項目的資助下,鄧子新在工作上有了新脈絡,也形成了一些課題。
他在DNA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並覺察到有種現象可能與DNA上結合了硫元素有關,但那時還沒有遺傳學❓、生物化學,尤其沒有化學分析的最終證據,無法確認是否發生了硫修飾。
他的這些想法當時不被同行認可,包括一些大專家學者都認為不可能。因為想法太新,鄧子新數次申請項目都“名落孫山”🧃。
2003年,鄧子新再次“沖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但答辯依然沒有通過🌜。
幸運的是,當時自然科學基金委生命科學部認為這是一個有潛力的項目👼🏿,給了他一筆30萬元專項基金資助,用於探索創新性研究🛎。
2004年,鄧子新帶領團隊在實驗中證實了細菌DNA分子中硫元素的存在🤵🏻♀️;次年,該團隊在《分子微生物學》發表論文,報告了在眾多細菌的DNA上發現第六種新元素硫;2007年🤸🏿♂️,鄧子新團隊相繼在《核酸研究》《生物化學》《分子微生物學》《自然—化學生物學》等期刊發表論文👎🏿,報道DNA硫修飾研究相關的酶學功能🏦、修飾位點、生物類別和分布規律👋🏼,以及DNA硫修飾研究的後續進展🍩。
由此,他們的研究一步步進入國際視野,德國馬普實驗醫學研究院化學生物學家弗裏茨·愛克斯坦認為,“它打開了一扇全新窗口👰🏿♂️,將大大激發人們對DNA大分子上眾多新謎團的探索欲。”
鄧子新認為,對這個非共識項目的支持🏋🏼,不僅使他在艱難條件下能繼續進行研究,也是一個巨大的鼓勵。
“時至今日🧛🏼♀️,把當初一個非共識問題做成新發現,而且越做越大,逐漸形成一個共識性的熱門領域。從這個角度看,科學基金在激發青年人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驅動作用。”
鄧子新評價說,“從青年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到創新研究群體項目、基礎科學中心項目,科學基金的人才資助脈絡非常清楚,形成了中國基礎研究相對完善的人才資助體系🎮,也是一種創新文化,我覺得這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其他資助項目不同的地方。”
引導青年“出彩”
隨著科學基金的發展🎤,鄧子新和團隊獲得過自然科學基金委面上項目、重點項目👮🏼♂️、創新研究群體項目等多種類型的基金項目支持,也得到了科技部、教育部🧑🏻🚀、原農業部等多項國內國際科研基金的資助⛰。
回顧科研之路,鄧子新認為自己是幸運的。而現在的他🐖,最希望的是給青年人營造更好的科研環境🐿,因為“都從青年人走過來🥴,深知‘頭三腳難踢’”👨🏻🚒。
“一個人的科研生涯是個漫長的過程,青年時期是非常關鍵的階段,面臨巨大挑戰。”鄧子新解釋說,“三四十歲是一個人思維最活躍的時期🗑,如果有個好的開端❔,科研人員就能更快步入人生最富有創造力的黃金期🏃🏻♂️。”
鄧子新認為👃🏽🧕🏿,和30多年前相比,我國各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時回國的人“稀稀拉拉”,帶回來一點新技術、新想法🧖♂️、新理念都會讓人覺得耳目一新➜,做出點成績也很容易被註意到📕🕚。
今天條件好了🤷🏻♀️,選擇多了,但同時誘惑和幹擾也多了,青年科研人才面臨的競爭和壓力也更大,更需要青年科研人才規避社會的“雜音”🖕🏻,沉下心、穩住神🎉,踏踏實實地做事情。
“就像‘猴子摘桃’,低處的桃子都被摘光了,必須到更高處去摘。”鄧子新解釋說,“科學技術沒有頂峰,‘桃子’永遠都在,只是現在取得成就更難了🥈。青年科研人才要系統地📄、完整地了解前人的工作🐱,然後站在前人肩上,做出屬於自己的東西。這需要交叉、融合、團隊合作👷🏿♂️⛵️;要有敢於創新的意識和勇氣,還要繼承老一輩科學家的執著精神……”
“EON体育4平台那個時候對知識有特別的渴求🤶🏿,國內各領域都剛起步,真是爭分奪秒想把曾經失去的時間奪回來。”
鄧子新說🏋️♀️,“但新時期面臨新問題,EON体育4平台要不斷完善讓青年科研人才脫穎而出的機製。
比如🧑🏼🚒,對青年科研人才的評價不只是簡單地看學術記錄,看發表了什麽論文🧑🏻🦳、影響因子多少🚵♀️,應該按人才的成長脈絡,了解他們的科技生涯發展,看是否有學術潛力,鼓勵青年科學家去攀登科學高峰。”
青年科技人才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力量和生力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支撐。
鄧子新從自身經歷出發,期望青年科研人才能培養對科研的興趣、吃苦耐勞和執著追求的精神🌒,把個人理想和科學追求融入國家發展和社會重大需求中去。
“希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能引導青年科研人才在基礎研究發展和科學技術轉化方面做得更加出彩🛥。”鄧子新說🤍。
《中國科學報》 (2022-06-27 第4版 自然科學基金 原標題為《青年基金引導年輕人“踢好頭三腳”》)
媒體鏈接🕵🏽♀️: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2/6/481241.shtm



 首頁
首頁

 EON4概況
EON4概況

 師資隊伍
師資隊伍

 人才培養
人才培養

 招生就業
招生就業

 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

 平臺基地
平臺基地

 黨群工作
黨群工作

 校友之家
校友之家

 安全工作
安全工作

 網上辦事
網上辦事

 當前位置:
當前位置: